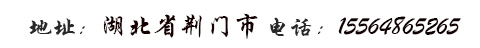憶恩師013
| 我們第三個單元,「出家修學」,最後用阿含經的一段文,我覺得這一段文對師父的描述很貼切,我們一起來把它念一下:阿含經這一段話,我覺得來描述師父這一生的修行非常貼切,「捨離恩愛」,我們一般人最難捨的大概是三個啦:一個是財富、另外再眷屬、還有就是色身,這三個。那師父說他當年要離開家的時候,他就夢到那個火車都倒了,他就覺得這是一個不是很好的徵兆,那當然修行人是比一般人敏銳,他也會觀察到整個氛圍,那時候也是很不忍,因為他說那時候祖母都已經九十六歲了,媽媽也六十幾歲了,可是如果不走大家都死啊,都死在那裡,所以捨棄什麼,師父能夠捨棄親情,捨棄這個眷屬。然後捨棄外財,師父說他當年把輪船公司,還有銀行股票都給妹妹,給他這個大妹妹,但是呢後來江山變色,你擁有那些反而是麻煩,反而會被鬥爭,所以妹妹也都不敢用,都沒有辦法,都要丟掉,所以師父就說一切的錢財受用都有定數的啦,所以師父也毅然地捨去這個外財、捨棄親情。還有呢,對色身,師父呢他善用這個色身來修道,但是他也不刻意去養護它啦。晚年的時候幫師父洗澡,你可以看出師父的整個手臂,雖然年紀很大了,可是還可以看出戒疤,整條手臂都燃戒疤,兩個手都有,可以看出說師父當年,應該是每一次的燃戒疤都有發一個願吧,發一個利他的願,或者是度生的願,或者是報答父母的種種,所以師父整個手臂都燃滿了戒疤,所以透過這一個動作提示什麼,自己的道念,還有自己最初的那一念發心吶,時時提醒自己。所以菩薩戒有講我們要「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。非出家菩薩。乃至餓虎、狼、師子。一切餓鬼。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。」菩薩戒有講到要做這個,但是我們凡夫菩薩怎麼有可能捨頭目腦髓呢,蚊子叮我們可能就扛不太了了,所以我們就什麼?我們用燃臂,一來激發我們的道心,二來也是降低我們的身見,不讓自己那麼愛著這個色殼子,當然要善用它,也不是故意糟蹋它,而是說你善用它,用它來修行,從有漏轉成無漏那就值得了。所以看師父整個手臂燃滿了這個戒疤呢,這個就知道師父他怎麼樣?他不但捨外財、捨親情,他對色身也能夠放得下,也能夠這樣做,利用它來修道,所以師父這是真出家啦。我們一般說我們出家是什麼,是出世俗家、出煩惱家、出無明家嘛,有很多的層次。一樣出家,那如果今天我們沒有辦法真實地生起這種對世間離染的心的話,那嚴格來說我們算搬家,不算出家,就是你從家裡搬到廟裡來住嘛,就是這樣,換衣服換一個衣服,然後內心的那一種心態也都沒有改變嘛,還是世俗人的想法,那一種出離的心沒有出來,乃至於利他的菩提心沒有出來,那這個就是比較屬於說就是剃髮染衣一個象徵啦,那以修行義來說,那真的是感覺像搬家一樣。當然我目前為止還是搬家而已,我不是說別人,我說我自己喔。攝御諸根,不染外欲,師父可以非常攝心。我以前聽會性老法師,會公,會性老法師講經,他好像在講那個《天台四教儀》還哪個地方有提到師父,他就講講,講到一半,講到那個攝心修定的那個地方,他就說:你們看過懺公嗎,他就是這樣眼觀鼻,鼻觀心,他在大眾這樣,然後他自己在寮房也是眼觀鼻,鼻觀心,不會亂看,不會亂攀緣。這是老人家,因為他有跟師父共住過,所以他說師父在大眾當中是這樣攝心,然後呢在寮房他也是這樣,裡外一如啦,不會說在大眾當中攝心,私底下在寮房就散心,不會。我們一般人都在大眾裡面要表現好一點,很有威儀,然後私下呢就很散亂,反正沒人看到,所以儒家講的慎獨。修行是對自己交代的,不是做給別人看,當然很多人在看是一個激勵,你要做得好,但是都沒有人在看的時候,其實呢,還能夠怎麼樣?保持那一念觀照,那這個人真的是內外一如,就是能夠慎獨。在沒有人看到的隱微處,你還是注意自己的身口,乃至於起心動念,那這樣的修行人會有成就,所以弘一大師也提倡慎獨。以前有一個跟也跟師父認識的叫聖心長老,聖心老法師,他在東勢有一個大願寺,他都拜地藏菩薩、修這個地藏法門,有一次他有來我們蓮因寺,然後來跟師父見面這樣,我們就請他開示,那他就很讚歎師父啊,他說:懺公呢很難得,當年我跟他老人家,就是聖心老法師跟師父一起去戒壇傳戒,就是當尊證,那他說呢師父也不跟人家談太多啦,有空他就對著牆壁拜佛,一有空,因為做尊證可能沒什麼太多的事吧,三師和尚比較忙,也是隨喜人家傳戒嘛就去配合一下,有空師父就對著牆壁拜佛。所以聖心老法師說他很讚歎說:全臺灣像懺公這樣用功的很少很少。那時候師父已經出家二、三十年了喔,還不是說剛出家。剛出家前兩年可能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可以做到,然後第十年剩下百分之五十,到第二十年剩百分之十五,然後到第三十年之後可能剩下百分之一啊,我們那個道心,其實要始終如一是不容易的,所以可以看出說,師父後面那個出離心有多強,所以這個支撐著師父隨時、隨處、隨地都不忘那一份初衷,那一念要離苦、那一念要解脫生死的心,常在心中,所以乃至於出家那麼久了去做尊證,還是一樣用功。不染外欲,就是能夠攝護根門,都攝眼耳鼻舌身意,然後自然對外面的色聲香味觸就不會染著。慈心一切,無所傷害。這個不染外欲,我想再講一下,我們看到師父的這種外顯的那個相狀,給我個人,我覺得第一個感覺就是師父很定、他非常得定、很安定,這個就從這邊來的,一個人要修定,他絕對不能,絕對要攝御諸根,不染外欲,就是根塵對境的時候,不能起虛妄分別,不能染著,這個是很重要。一個人要修定,絕對離不開這個主要的範疇,你說一天到晚到處亂看、到處亂聽、到處抓、到處攀緣,那他怎麼可能定,他不可能,他沒辦法制心一處啊,絕對不可能。所以一定要先守護根門,這很重要!這一開始,像論上講的,烏龜牠要防止被野干吃掉,必須要把頭啊、腳啊、尾巴剛好六個收起來,才不會被傷害到,那就比喻我們一個修行人,你要怎麼樣?你要守護根門,要注意你的六根門頭,必須時時守護好,就像烏龜要把那個腳啊、尾巴、頭收起來,這樣野干,就是煩惱、就是外境,牠才不會傷害到你,這一樣的意思,那你這時候就會有定啊。慈心一切,無所傷害,因為我們見到師父的時候,師父是一個已經修行幾十年的老和尚,非常的有威德,那沒有很久、長時間地接觸,就是看那個樣子、外相,師父很威嚴、很有威德。但是我曾經問過師父的妹妹,我說老菩薩,大法師……她都稱呼師父大法師。我問說:大法師在俗家,在你們家的時候,那時候他的脾氣呀性格是怎麼樣?我好奇問一下,會不會很有威嚴,因為是老闆嘛。她說大法師在家的時候就非常溫和、非常慈悲,他對任何人連一句重話都不會講,她說師父在家就是這樣的性格。因為我們,經過幾十年師父這樣修行,所以師父那一份本然先天帶的那種悲心、慈悲,對人那種體貼、那種慈悲,本來就在,那加上幾十年的修行,所以他有時候會示現怒目金剛相種種,當然我們會以為說師父就很嚴厲,其實從老菩薩這句話就可以知道,師父他在家就是很溫和、很慈悲的,對任何人都不說一句重話的,慈心一切,無所傷害。然後遇樂不欣,逢苦不戚,一個修行人他遇到順境,遇到如意的境界,他不會起顛倒,不會執以為實,不會在那邊沾沾自喜,那師父經過這種世間的大風大浪,世間的這一種成敗啊,師父都經過了,所以呢,了知無常,遇到這些順境,他也不會覺得滿心歡喜,不會,不會起這種執以為實,起這種顛倒。那逢苦不戚,師父剛從東北一路往北方、江南這樣到臺灣,我們可以想一想,那種氣候差異有多大,東北是大陸型氣候,又乾又冷,臺灣是又濕又熱,這種截然不同的這種氣候。一般我們有出過國的就知道,如果你到一個氣候完全差異很大的地方,你很容易生病,非常容易生病。所以師父剛來臺灣的時候他說他得了那個痢疾,就是一直拉肚子,拉到都拉血了,那個就很嚴重了,所以後來師父的二妹妹就接他到臺北,來調身體,調了一段時間。還有在南部也脾腫啊,就是脾腫大,也蠻嚴重的,還到那個三軍醫院去檢查。還有在光德寺那一邊,那邊曾經跌斷腿,就是摔斷腿,這些都是這種苦啊,一種疾病的色身的這種苦。可是師父都能逢苦不戚,他說那時候就是背普門品,然後求觀音菩薩。師父就說有病的時候,我們求觀世音菩薩好,希望這個病呢,能夠蒙菩薩的加被能夠超越、能夠遇到好的醫生、或好的助緣來。師父說他腿斷掉的時候,也很怕將來沒有好了,以後出來撚香,然後腳一跛一跛的,人家說怎麼有一個跛腳的法師出來這樣,所以是擔心說自己是一個出家人那個形象不好,還不是說只擔心自己這個色身。所以那時候他說他念普門品,結果沒多久就遇到一個赤腳醫生,把他接骨,接一接,誒,他覺得很癢,沒多久就好了。所以師父也是教導我們,我們以後要是遇到什麼病難呐這些障難,我們就念觀音菩薩。師父也開示過,我們到一個新的地方,或者到一個陌生的環境,要去那邊辦事啦種種啦,求觀世音菩薩好,因為觀世音菩薩是道場主,師父這樣講。所以逢苦不戚啦,師父色身的這種苦啦,乃至氣候這麼大的差異啊,還有文化語言的這種不一樣,師父都能夠安忍,能忍如地。為什麼用地呢?大地就能承載一切、包容一切、接受一切嘛,所以不管你是美的、醜的,不管你是高、低、大、小,不管你是好的、壞的,或者你是陰天、或者晴天,反正所有一切降臨到大地這邊來,大地全然地接受。那一個修行人就應該如此,能夠安忍一切的順逆、苦樂,像大地一樣不動。所以這個忍,還不是只有忍耐那個逆境,順境要不要忍?也要忍啊。所以我們這個娑婆世界,為什麼叫堪忍的世界,我們娑婆世界,我們要叫堪忍,就是很難忍,但是我們還在這邊一直忍,早上也要忍、中午也要忍、下午也要忍、晚上也要忍,年輕的時候要忍耐,然後年紀慢慢長大也要忍耐,年老了還是要忍,所以我們整個生命過程,無時無刻不處在一種我們需要去忍耐的狀態,所以叫堪忍、堪忍的世界。那也因為我們能夠忍,所以我們才有可能超越,如果我們今天不耐煩了、不想忍了,那我們就放棄了,所以我們的修行就會有障礙啦,有時候,往往我們一念的不能夠忍,然後衍生出什麼?後患無窮的障礙出來,所以這個忍很重要,安忍,這也是師父常常勉勵我們的話,就要學習安忍,當然這一點我做得非常得差,故名沙門,這個叫沙門。好,我們看下一段,我這是簡單描述啦,因為大家可以去看師父有一個影片介紹蓮因寺的略史有稍微提到,還有蓮因寺有整理懺雲老和尚的開示錄,後面有一段師父的略傳,也有提到一些比較詳細,我這邊大概帶過。師父說,這是我聽師父描述,說他剛來臺灣的時候是先去法雲寺掛單,法雲寺在現在苗栗,那時候是斌宗老法師住持,他就提兩個包包就到法雲寺,那一到的時候,他說有個人就用臺灣話說:外省仔來臺灣,就死路一條,已經是無路可退了。因為已經是最後一個島了,師父說他當時不懂臺灣話,他就問旁邊的人說,他講這是啥意思,那個人就翻譯給師父聽,師父一聽,師父說我那時候心裡就這樣想,我們更應該努力呀,更應該奮發,更應該要用功修行啊,師父就起這樣的念頭。對呀,因為已經無路可退了,背水一戰啊,就像這輩子不往生,再來沒機會了,就是類似這樣的一種味道。所以最初是到法雲寺掛單,然後後來師父又南下到大岡山,然後也住過光德寺,也曾經到東山寺,屏東有一個寺院叫東山寺,在火車站附近。我那時候在屏東讀書,我曾經去那個廟,那個廟也很有歷史,看起來很老。那有一次去蓮因寺的時候,師父好像都知道你跑去那裡,那個大圓鏡智裡面的資料庫提出來,他突然說:「你有沒有去過那個東山寺?在屏東有沒有?」我說「有,弟子有去過幾次。」他說:「我年輕的時候也去那邊跟人家結過緣呢」,師父就講,他曾經也去過東山寺,所以我這邊寫南下高屏。然後埔里觀音,齊聚修行,我這邊為什麼用齊聚修行,我講埔里觀音,師父很敬重兩位大德,一位是印光大師,一位是弘一律師。印光大師就是淨土的代表,弘一大師就是律宗的代表,就是持戒念佛這個方向,這個修行的大方針。所以師父在埔里觀音山蓋那個茅蓬,取名叫做印弘茅蓬。在那一段期間,師父在印弘茅蓬那一段期間,在住觀音山那一段歲月呢,有很多這些老參或者是出家師父,跟師父結緣都是很特別的,甚至是一輩子很久的緣,大家最知道就是菩妙老法師,元亨寺的菩妙老法師。師父曾經在南部住過嘛,然後也跟菩妙老法師有認識,那時候菩妙老法師想去大陸參方,可是大陸就因為因緣變了沒辦法,所以那時候就跟師父約定說,將來如果有因緣我們共住啦,我們建一個小小的這種地方一起來修行,後來師父埔里觀音茅篷,印弘茅蓬建好了,就邀菩妙老法師,菩妙老法師就來住了,就打同參這樣。那時候師父常常在大眾裡面,讚歎菩妙老法師很有道心,為了練那個雙盤腿、雙跏趺,結果那個皮肉都戳破,都流血了,骨頭都露出來,你可以看出師父他們那一代的修行人那種用心啦。我們現在稍微疼一下就趕快放下來,然後擦那個撒隆巴斯(跌打藥)啦、什麼藥膏擦了很多、或抹很多的什麼舒筋的那些藥膏,人家老法師他們盤到骨頭都露出來還在盤呐,我們真是差很多。師父說,老法師很有道心都不倒單,晚上沒有躺下去睡,他怎麼知道?因為有一次老法師就盤腿,結果呢師父在隔壁房,聽到砰的一聲半夜,怎麼回事,隔壁發生什麼事?師父就過來看一下,喔,菩妙老法師因為很用功雙盤腿,不要躺下來睡,結果半夜打瞌睡,結果就整個人倒栽蔥這樣倒下來。很難得啊,我們連這種精神都沒有啊,我們連想試的精神都沒有。所以這個是菩妙老法師很有道心。後來菩妙老法師快圓寂前,有人幫他,他有口述他這輩子的一些事情,人家常常提到這一段,他跟師父打同參的過程,師父讚歎他。結果菩妙老法師他就講出來,他說懺公才了不起呀,懺公呢,他九十天行般舟不坐不臥,你可以看出師父他行這種苦行都沒跟人家講,他倒是一直讚歎他的同參道友,所以可見師父他很低調。這個時間不只菩妙法師來親近師父,還有淨空老法師也是這個時間,不過淨空老法師那時候並不是出家身份,他是在家居士去親近師父,大概住了半年,還有如悟長老也是這時候也去親近師父,還有關老師,跟師父很有緣的一個住新竹的關世謙老師,都是這個時候跟師父結的這個緣,所以齊聚修行這邊這樣寫。那住這個觀音山這段期間,師父說他這時候的心境呢,跟當年從東北到江南,去靈岩山寺那時候心境完全不一樣。師父說他當時從東北家裡出來到北方,一直到江浙一帶,他到蘇州靈岩山寺,看到整個大殿那麼多師父在做晚課,他在那邊走路啊,在那邊眺望,他心裡很感傷:真的很無常,我從東北這麼一路竟然來到了江南,他覺得感歎人世的那種無常。但是師父說,他這時候在埔里觀音山住山的時候,心境就不一樣了,那種感傷那一些就沒有了,這時候心境是非常光明的,都是正向的。師父說有一次呢,這個大家可能都聽過,他拜完佛,然後到外面的茅蓬石頭上打坐,那一輪明月從東方冉冉升起,然後看著埔里的萬家燈火,這時候師父突然覺得「三生有幸啊,今生為僧」,真是太幸福了,能夠出家修行,這時候師父那種心境就沒有像之前剛出家、剛到南方那種心情,就不一樣了。所以可見說我們修行人的心呢其實是一直在調適的,我們越向道這邊去用功,越向法這邊去深入,我們的心呢就越開朗、越光明、越開闊、越自在,那如果我們一直局限在世俗,一直抓著世俗的這一些情啊、人啊、事啊、物啊,那我們就越來越閉塞、越來越感傷、越羸弱啦。所以可以想說,你看還是一切唯心造嘛。三十幾歲的師父跟這時候四十二歲的師父就不一樣,他那種心境就不一樣了。我也曾經有一次下午幫師父泡腳,忽然間,不過我覺得也是好啦,那時候有一點就是不太知道禮貌啦,因為反正剛去嘛什麼都問。我就說:「師父您那時候住茅蓬有什麼滋味啊,有什麼感覺?」因為我也很想住茅蓬,那時候每天都在想那個好像很好這樣,當然跟我們想的不一樣。師父說:「我那時候有法喜、有禪悅」,他就這樣講。然後我說:「那是什麼感覺?」他說:「我那時候,我就每半個月去埔里買個米,背個米袋」。以前是要自己去米店買米,不是像現在去7-11買一包啥,那都要去米店去秤,然後再自己背回來。結果他說半個月就去埔里街上買個米,結果每次他說只要走到山腳下,走到山腰的時候,他的內心是什麼,我後面有寫:「載欣載奔」吶,載欣載奔是什麼?就是好像要跳躍起來,非常得高興,希望趕快回到茅蓬繼續去用功。你看這表示說師父真的用功得很好,很得利、很有法喜、有禪悅,才會有這種載欣載奔嘛。不然我們一般住久了,今天到那裡撈一撈好了、透透氣啊,不管住僧團、住茅蓬都一樣,住久了覺得很膩呀。哎呀,還沒上山,覺得寺院很好,這裡滾滾紅塵好煩啊;結果上了山覺得,哇,這麼無聊啊,還是山下好像也不錯。那你看師父他是說,哇,載欣載奔,很想再回到那個地方繼續用功,所以有禪悅,有法喜。可是世間上的事,無常還是一直考驗著師父啦,這麼好的環境,然後也這麼安定用功充滿法喜,可是後來就發生八七水災,整個茅蓬就沖壞了。沖壞以後呢,師父說菩妙老法師他就回南部了,師父他就到太平,現在臺中縣太平鄉那個地方。那到那個地方他說是冬天去找的,因為在山溝,冬天的時候不覺得熱,可是一到夏天,哇,好悶好熱啊,師父說他在那邊住了三年,因為後來親近師父的人越來越多,想跟師父修行的,那時候說大概八、九位越來越多,所以師父就想說,很多人也建議嘛找一個比較固定的地方,不要搬來搬去了,所以那時候師父就開始要找地方要蓋一個道場,就這樣。那住太平那一段時間,聽師父描述說,那地方因為山溝,然後濕熱,那個蛇非常得多、很多蛇,有時候師父說他在打坐,坐一坐,突然間,那個真的是茅蓬吶,就掉幾條蛇下來,然後要下座了,旁邊呢有時候,左邊一條、右邊一條,鞋子也有蛇,所以都要注意、要趕一下,不然可能不小心會跟牠有擦撞麻煩。那從師父這個描述就可以看出說,在蓮因寺蛇也很多,我們常看到,那個蛇我和阿闍黎去巡水,你這個禮拜去巡,那隻青竹絲就在那邊不動,下禮拜去牠還在那邊,牠是很靜的、非常靜,當然那是癡啊,愚癡啦,可是蛇是那麼靜的,你只要風吹草動,牠一受干擾就會跑了。那表示師父是非常安定,他非常靜,所以那個蛇在旁邊,都沒感受到這是有一個人在這邊,所以牠就跟著在旁邊,可能牠也入定了吧,就這樣,或者牠要取暖,師父因為打坐身上的這個氣脈通達,然後身體的熱度夠蛇過來取暖;或者是師父的悲心特別得強,那時候修慈悲觀,所以這些蛇都感覺太溫暖了、都齊聚過來。當然這我個人猜測啦,不過這個就是什麼?師父的心很靜、很定才有可能這樣。不然不相信,現在放幾條蛇你坐坐看,牠會不會在你旁邊待,絕對不會啦,牠一下就跑了,因為你那麼動嘛,牠一觸覺到,哇,這個太躁動,這個不是我待的地方,牠要找一個安定的地方去。所以後來就是太悶、太熱了,然後後來師父就,也人越來越多,所以就決定找一個地方,然後後來就找到什麼?師父從金山野柳,從北部金山野柳一直找到這個南部鵝鑾鼻,這樣找了兩年都沒有一個很確切的這一種理想的地方。後來有人寫信跟師父說,請人幫忙比較快,因為大家分散在各地看有沒有好的地點。後來在水里有一個〇〇〇老居士,他就介紹現在蓮因寺那塊地給師父,所以這個老居士師父也常念他,師父的蒙山迴向名單也都有他的名字,這真的蠻特別的。我們注意看師父的那個蒙山迴向名單都有固定的幾個人,有什麼老王啦、二伯父啦、這什麼某某老居士、或某某法師,我曾經問師父說:師父你這個蒙山名單,怎麼這些人都長期在念?爸爸媽媽當然不用講,哥哥,這些人是什麼特別的緣?師父說這個人跟他是什麼緣,這個人是曾經我腿斷掉,他背我,背我去看醫生;這個人又是我什麼時候然後幫助過我怎麼樣,而且師父都把他名字,寫在蓮因寺的蓮位上面,很特別,可以看出說師父他那種知恩報恩的心。當然可能不是實質回饋你什麼,而是用他的修行回饋你,所以一輩子這樣幫他迴向。所以我開玩笑,這些人真的是賺翻了:投資到什麼績優股,超績優股,讓師父一輩子幫你做功課迴向,那還得了。這真的是太……不過他們也是一念的虔敬心啦,也是因緣嘛,我想他們不會想說做投資啦,這是我開玩笑的話,而是說如果以世間的投資報酬率來說,哇,這個真的是超級績優股,師父一輩子幫他這樣用功,每天做功課幫他迴向,那不得了。當然〇〇〇老居士也是其中一個,師父說這個幫我介紹蓮因寺這塊地,那他的第二代也都護持師父到現在。所以沉潛自修這一段,我就引用那個《證道歌》,永嘉大師《證道歌》講的兩段,還有一個北宋的一個法師寫的,這三首詩來說強加附和也好,就是揣摩一下師父修行的那個韻味,我們一起把它念下:這是永嘉禪師,你看他說呢修道人,不一定是出家人,我覺得我們用修道人的眼光來看比較寬廣,一個修道人呢雖然物質上世間的這種貧窮,並沒有那麼豐富,並沒有那麼具足,口稱貧,就是人家說你是個窮光蛋,你不是富有的人,實是身貧道不貧,雖然我的這一種資財受用不是那麼的豐饒,但是呢我的道,我內心有戒定慧的這個功德,所以其實我一點都不貧乏。那為什麼用這一段來描述師父呢?這個是我以前聽圓因老法師講的,圓因老法師是民國五十三年去蓮因寺出家的,他說呢他那時候來蓮因寺,整個蓮因寺只有四個人,師父,還有我們現在最老的師兄,現在蓮因寺的方丈性因法師,還有他,還有他弟弟,就四個,那他都做典座,煮飯給師父吃,他說常常要煮飯了,米缸裡面沒有米,米缸沒有米那怎麼辦呢?老法師說他在家賺很多錢,他也很會賺錢,他就寫劃撥單,寫一個無名氏一次捐五萬給師父,那時候的五萬吶,那時候五萬跟我們現在,可能不知道我們現在多少,算是有一筆數目。結果呢他說師父應該是知道,所以後來師父給他們在上面蓋茅蓬。我說:那時候怎麼會沒有米?他說就是沒有米啊,師父也沒有跟人家化緣呐,有時候很久才有人來呀,師父從來也不跟人家開口,也不會跟人家說什麼,可能師父也知道說這個徒弟會護持吧。所以他也很大方一次就五萬匯給師父,而且寫一個無名氏喔,所以他開玩笑說,我們今天能夠住這個茅蓬,應該是當初師父知道這個事。而且我跟你講,我跟我弟弟蓋這個茅蓬也是花五萬塊,蓋兩間茅蓬剛剛好,所以可以想像說師父那時候,他真的不是那麼的優渥啦。那時候蓮因寺也沒有蓋念佛堂、更沒有大殿、更沒有蒙山殿,那時候就一排矮房子就這麼一寮,他說他曾經做這個動作,所以師父那時候真是窮釋子啊,真的是窮,不是很富有的,但是師父內心有法喜嘛、有智慧、有這個禪悅,所以身貧道不貧。貧則身常披縷褐,一個修道人呢外表貧,外表並沒有什麼豐富的物質,身體常常披著這個壞色衣,出家人的壞色衣。然後呢道則心藏無價珍,但是透過戒定慧的這個道呢,找回我們本具的佛性,我們這個心本來就有無量的這種德能啊,無量的這種寶藏,所以就像一顆摩尼寶珠一樣。所以一個道人呢他雖然外表受用不好,沒有很多的這種資財,可是呢透過他戒定慧的訓練、戒定慧的熏修,慢慢地找回我們本具的佛性,無量光、無量壽那個心,這個是什麼?無價珍呐,這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,所以叫無價珍,就像一顆摩尼寶珠,所以這是修道人最快樂的。他不會被世間的這些色身香味觸,這些財色名食睡所綁,他內心是有禪悅、有法喜的,你看這些高僧大德都是啊,廣欽老和尚住洞、虛雲老和尚住山,都是這個樣子。再來,這個永嘉大師呢,另外有這麼一段,這個我們可以把它想成一幅畫你知道嘛,就是在深山在寂靜處,蘭若就是寂靜處,岑崟幽邃長松下,岑崟就是那個山勢非常的高峻,很高的那種高山,幽邃就是很偏僻、很僻遠的地方,在那種深山僻遠的地方,山勢高峻的那種深山群當中,群山當中,有一個修行人,在那一棵老松,長松就是古老的松樹下面呢悠遊靜坐野僧家,悠然自得地經行,在那邊打坐,無拘無束地這樣來修行,你可以想像這一幅畫那種樣子。然後闐寂安居實瀟灑,這個修行人呢雖然住在這種深山蘭若,那種人煙罕至的地方,但是因為他用功得非常法喜、悠然自得,所以呢他內心怎麼樣?淡泊,闐寂,闐就是淡泊的意思,然後寂就是寂靜,淡泊寂靜,然後安定法喜,那這時候怎麼?自在灑脫,因為沒有被世間的紅塵所綁。這時候你可以想像這一幅畫的場景,這一個修道人。我們有時候會想說,沒有世間的東西是不是會很痛苦?當然我們不可否認,如果你今天窮到都沒有飯吃,以我們一般人來說一定苦啊。可是外面的資財不是決定你快樂或者幸福的絕對的標準,絕對不是這樣。我們看一看本師釋迦牟尼佛,我們本師啊,釋迦牟尼佛來降生,他一輩子就只有三衣一缽,隨身就是這個東西而已,但是我們有人比釋迦牟尼佛更快樂、更自在的嗎?我想沒有。所以可以肯定一點就是說,外在的物質條件並不是決定你快樂自在的最大的因素,它只可能是一點微少的一個助緣,真正的自在、跟真正的幸福快樂,是來自於你內心的安定、內心的寂靜、內心的那一念智慧光明,這是一個人真正得到幸福、自在、快樂的主要原因呐。你看本師只有三衣一缽,但是釋迦牟尼佛這麼的自在,這麼的灑脫,我們就可以想像。我們再看第三首詩,師父生前也蠻喜歡這首詩的,因為裡面有兩個雲。千峰頂上一間屋,層巒疊翠的群山當中有一間茅草屋,這個老僧不一定是很老的出家人,這個老參師父啦,就是修行得利的那一種修行人,一個老參師父呢住在裡面,住在這個層巒疊翠的群山當中的這個茅屋當中。然後老僧半間雲半間,因為雲霧繚繞嘛,所以有時候整個房子一半都被雲霧占滿了,這種情形我們也可以想像,我們到比較有雲霧的地方,有時候突然間,山上那個氣候變化很大,那個雲,雲霧一飄來,整個屋子裡面都是被雲霧繚繞,所以這裡形容得很好,老僧半間雲半間。昨夜雲隨風雨去,昨天夜裡呢,雲霧變化、凝結成雨水,所以隨著風就消失了。雲雖然豐富多變,能變出各種的相狀,但畢竟還是不如老僧,這一念靈知的真心、對一切境界寂然不動,而卻又了了分明;雖然了了分明,但又寂然不動,這麼的清淨悠閒,所以這一句話到頭不似老僧閑。雲是變化萬千的,這個就描述什麼?就是世間的生活,世間色聲香味觸這些五欲的生活好像很豐富、很多彩多姿啊,但是它無常、它變異,它到頭來是苦,所以還不如這個老僧,他在山上他的心,這念靈知的心,面對一切的境界寂然不動、又了了分明,那樣的清淨悠閒。所以這個是一個老參師父,他一種寂照的功夫,他內心寂然不動,但對境界又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,雲來了、雲走了他都知道,這好比一個鏡子在這邊,誰來了、誰去了,它都了知。但是鏡子不會留下任何的痕跡,但是同時它也不會排斥任何的境緣,是不是這樣?這就是一個修道人,他找到他接近本心的那種狀態就是這樣,我們一般說用心如鏡,他的心像鏡子一樣,漢來漢現、胡來胡現,來者不拒、去者也不留,不著痕跡,但是又清楚照了,這老參師父就是這樣。所以「昨夜雲隨風雨去,到頭不似老僧閑」,雲彩任它千變萬化、多彩多姿,還是白忙碌一場,就像世間功名利祿啊,到最後還是換來一場空,到頭不似老僧閑。我想用這個詩體會體會師父那種心境,當然師父的心境可能更高啦,我們只是用這樣很勉強的言語來形容。好,接下來我們來看弘化利他這個地方,不過時間也差不多了,我們就講到這邊好了。這個地方,我剛好前一陣子遇到一個事,跟師父住茅蓬這段時間有一點關聯,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有一陣子身體很差,我想說,唉,身體很差,師父說拜佛,但是我們的信心沒有像師父這樣,說慚愧真的很慚愧,所以想說不然練一個什麼來調一下身吧,想說聽說練太極拳對身體很好,埔里有一個隱居的高手住這裡,就透過人去找,那他就說好。陳師父說:師父你幾點來找他。我一去到他那個地方,他看看我他就說:師父你那裡出家啊?我說我在水里。他說懺公師父那邊嗎?我說對。他說:哎呦你不用學啦。我說:我就是有需要才來找你要學啊,你怎麼說不用學?他說:我跟你講,你們修行人,你們有你們的專業啊,你們可以用你們的專業超越啊。我說:我們的專業?他說:你們拜佛啊、打坐啊、繞佛啊,一定可以超越。我說:你有在拜佛、繞佛、打坐?他說:我沒有。那你怎麼會講這個話?他說:我可以篤定地講,絕對不會比練太極拳差啦。我說:你怎麼這麼有信心啊?他說:師父我跟你講,我四歲就開始練拳了,我們家我爸爸是這個地區拳術的領頭羊,第一名的高手,所以我們家從小就有師承,我是真的是不得已,我從小就被逼要練拳。然後他說:懺公師父當年住埔里,住在那個圓通寺後面那時候,我的舅舅也是武林高手,他的聲音一吼可以幾百公尺以外都聽得到,非常得渾厚。我說:那這有什麼關係?他說:當年我舅舅也認識師父,也護持師父,算是半護持,他不是正信的三寶弟子,但他對師父好印象。所以他每次,他就住山腳下,他每次要去埔里辦事買東西,他就會在山腳下,那時候也沒有大哥大說打一下,或者傳line(類似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zhongjiefenga.com/zjfgy/972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一味中草药猪苓
- 下一篇文章: 最忆是杭州杭州文化旅游重庆推介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