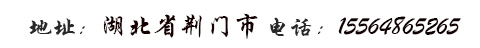优秀小说玻璃屋
|
彭洋挂号 http://m.39.net/news/a_9385547.html (小说开头掉了两句话,补在留言处)虽然离市区远了些,但离病毒也远,也算是个避风港吧。 这是疫情来后的第三个春天。园里的玉兰、早樱、桃花,一如既往,纷纷绽放,到处都是开花的树。连街上也是,走着走着,就能看见银行或商场门口一棵貌不惊人的小树,忽然炸开满树繁花。人们透过厚厚的口罩,也能感受到那股子馥郁的气息,春天里独有的气息。 在她工作的植物园,除了玉兰、早樱、桃花,最知名的还属郁金香,一百多个名贵品种,十几万株,全盛时,一片流荡的、姹紫嫣红的花海,几乎要把整个春天燃烧殆尽。园艺师还会把喜林草、紫罗兰、角堇、羽衣甘蓝等植物,与各色郁金香进行搭配,营造出某种飞翔或升腾感,好像这些春天的精灵随时可能扬帆起航,或原地组建一个自由王国。 如今,还有不到半个月时间,郁金香便进入最佳观赏期。去年花期时,因疫情而限流,园内游人寥寥。那二十几天里,她们这些工作人员就像游魂,不在办公室里坐着,而是去那花海中飘来荡去,手机里尽是各种俯拍、平视和仰拍镜头,或以长焦镜头拍摄单朵,或以微距摄下局部细节。每一朵花都那么美,真想一朵朵拍过去,把它们完整地保存下来。她为自己这种近乎疯狂的想法感到羞愧。 这个春天,她和同事们一如既往筹备花展,包括主展区的景点布置、配套景观的调整以及花木造型的设计,但心里总有些不安,意外和隔绝随时可能降临。过去两年里,这种消极情绪几乎主宰了园区内每个工作人员的生活,一开始出现时,几乎无人察觉,到最后酿成无力挣脱之势,已经晚了。 唯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,花草树木比他们更有耐心,也更热情,不肯虚度任何一个春天。随着枝上新绿渐深、郁金香花期临近,她在园区里漫步的时间越来越长。有时候,整个白天她都在花草丛中度过。 那天黄昏,她坐班车返城,却没有急着回家。小区附近有个公交站台,刚刚改造过,流线型结构,给人一气呵成之感。自从疫情暴发后,街上总是空荡荡的,人们不是待在汽车里,便是在自家房子里。 她临时决定去城西的湿地公园。已经想不起来上次去那里是什么时候,只记得浓郁的橘花香味在空中飘荡,绿树的枝上像是覆了一层细雪。还有带白色条纹尾巴的鸟儿猛地撞开树枝,滑向那片绿草地。过去的时间被揉碎了——这些,很可能是多次场景的组合或叠加。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等公交车来。公交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有一大片绿化带,长着高大茂密的香樟树,这是常青树种的落叶季节,树底下铺着细密的黄绿相间的叶片,紫黑色的香樟果散落一地,像是积了一层黑雪。期间,来了几辆从郊区方向开来的公交车,车上乘客寥寥。而她所等的班车迟迟未来。透过树与树之间的间隙,她看到夜色一点点漫浸上来,阴影与树影逐渐融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。随着时间流逝,树的轮廓变得粗重、模糊,被夜色放大,无限晕染开去。一种恍惚感忽然袭来——好像,她不是在城市的马路上等车,而是置身山林深处。人群隐去,建筑物消失,只有暝色中的树木,排列成行、成阵,逐渐取代这个喧嚣而杂乱的世界。 她居住的城市,放眼望去都是平原,地平线那端没有山,山在几百公里之外。这个黄昏,她忽然感到山的存在。脑海里储存的相关画面,一点点涌现,将她拉入另一个世界。这之后,好几个黄昏,她散步路过那里,都要在空无一人的站台上端坐片刻,好似一个失魂落魄的失忆症患者,要从几株行道树中辨认出树林的影子,并从中获得庇护。几天之后,她在家里吃晚饭,单位打来电话。三天前,植物园里来了一名有疫区旅居史的游客,刚刚被确诊。园区要关闭七天进行消杀,相关人员还得被隔离。那天,她恰巧在市里开会,流调名单上并没有她的名字。视频资料显示,那名四十几岁的男子,在一棵盛开的玉兰树下,坐了大半天,并没有进入任何密闭场所,连卫生间也没去。但疾控中心的人坚持认为,存在传播风险,必须关停。挂断电话后,她将桌上饭菜一扫而光,两年来,头一次有如释重负之感。至少一个星期不用上班了。之前,她总担心自己会被隔离在单位。那段时间,很多人出门都随身携带洗漱包,她也如此。如今,当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,她却发现自己成了漏网之鱼,被隔离之网剔除在外,根本没她什么事,连共情的机会都没有。她坐在家中,徒然刷着手机,单位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zhongjiefenga.com/zjfpz/1092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内地即将成为今年全球最大电影市场,家乡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